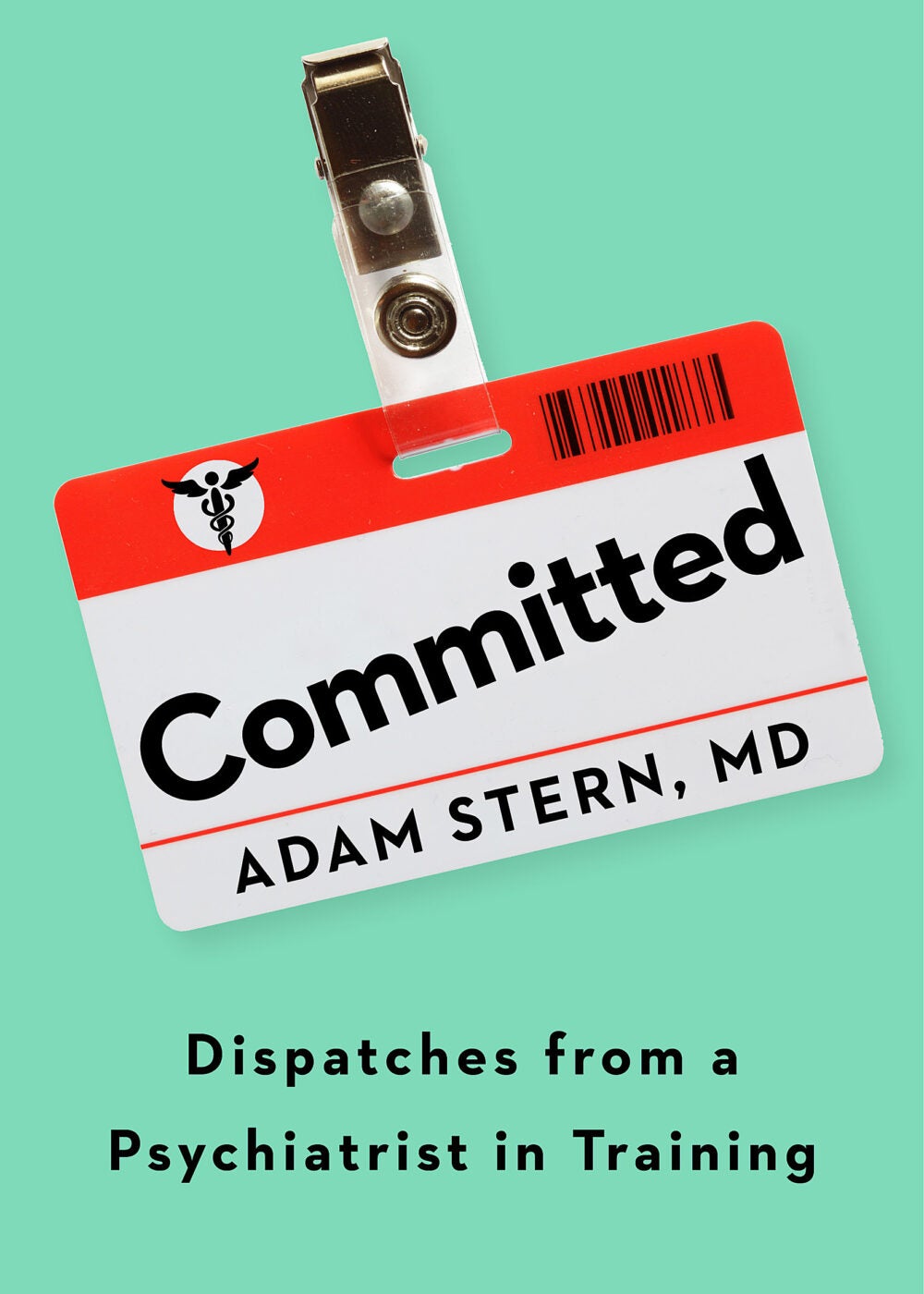摘自亚当·斯特恩(Adam Stern)的《承诺:一名接受培训的精神病学家的报告》(Committed: Dispatches from a psychiatric in Training),他是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贝伦森-艾伦非侵入性脑刺激中心(Berenson-Allen Center for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的精神病学应用主任,也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助理教授。
在去急诊室的路上,我在大厅的咖啡店买了两个牛角面包和两杯咖啡。我输入了五位数的密码,进入了“地堡”,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精神科的工作人员在靠近急诊室的时候会躲在里面完成工作。在那里,我发现高级住院医师丽贝卡(Rebecca)茫然地盯着白板,上面写着等待就诊的病人名单。
“早餐?”我问。
“你停下来喝咖啡了?”没时间喝咖啡了。看看这个。看。”
有八个病人等着看医生。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白天有一整个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团队,而让一名二年级的住院医生整晚都在担着担子。”
“嗯,还是个实习生,”我补充道。
她瞥了我一眼。
“对了。和你。我们最好分而治之。你把这四个人带走,没先把案子交给我之前不许让任何人回家。明白了吗?”
“狐猴”。
但她已经带着她的笔记板出门了。我叹了口气,喝了一口咖啡,看着丽贝卡给我分配的四个病人的名字。
“[脏话]?”我问。
这几乎是我上个月的所有病人名单。简,保罗,金吉和黛博拉都在几周内回到了急诊室。
“不可能。”
“不可能是什么?房间另一边的一位女士从她的电脑上抬起头来问道。
“哦,没什么。我只是很惊讶看到其中一些名字。”
我把目光从写字板上转到那个女人身上。
“你一直坐在那儿吗?”
她点了点头。
“你是谁?”
“我是南茜,找床人。我发现这些病人入院时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城里。你得对我好点因为我是这些病人离开你急诊室的唯一途径”
“很高兴知道,南希。要一个牛角面包和一杯咖啡吗?”
“好吧,非常感谢你,”她说着伸出了手,眼睛仍然没有离开屏幕。“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我被分配的病人名单,他们——他们是我在南部4号医院照顾的所有病人。”
“所以什么?”
“嗯,我让他们出院的时候,他们都很好。我想我只是很惊讶看到他们回来了。”
“孩子,他们总是会反弹的。”
我咬了一口羊角面包,拿着打印机旁边的剪贴板离开了。
简成功地避免了法庭强制的厌食症治疗,她是我名单上的第一个病人,也是我在穿过绿区(Green Zone)的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房间。她当时21岁,凭借自己的才智和职业道德进入了哈佛大学,但她的厌食症让她崩溃了。
就像急诊室这一区域的所有病人一样,她被关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轮床。她母亲坐在她旁边,眼睛浮肿地盯着地板。
“简,”我一进门就宣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看上去比离开时更瘦更虚弱了。那时她重78磅。
“哦,太好了,是你。”
“是我。”
我们互相打量着对方。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到急诊室来了?”我问,心里明明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是白痴吗?”你需要我再把一切都告诉你一遍吗?”
“我觉得让我的病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是很好的。”
“我不是你的病人。我见到你只是因为你是这里唯一的白痴。”
“好吧,简。所以,帮个白痴,好吗?在南街4号,你告诉过我事情会怎样发展,你是对的。现在怎么样?”
“时代变了。这一次医学和精神病学将会在我是否足够稳定的情况下进入精神病学进行一场激烈的较量。医学部会说我很好,可以住进南方4号医院,精神科会说我的体重指数太低,还有我的心率和血糖。”
“谁会赢?”
当然,“精神病学。医学上,他们从不接受任何让他们紧张的人,而我让人们紧张。”
“好吧,简。谢谢你给我指路。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
这次我和她妈妈目光接触,她只是摇了摇头。
“你的鞋带开了。”
我低下头。再次,简。我弯下腰系好鞋带,然后抬头看着她。
“我会让你休息的,如果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就喊一声。”
“让我休息一下吧?”
她很会胡言乱语。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着,下了车,关上了滑动玻璃门。
接下来是保罗,一个伤心欲绝的罗密欧,他的女友搬到了瑞典。当我走进保罗的房间时,他告诉我他又要自杀了。我问他是否还在伤心,他说还在伤心。
“当你在乎的人离开了,这是非常困难的,”我说。
“这次她没有搬走。”
“这一次吗?”
“有一个新的人。嗯,没有。不过她把我甩了。”
保罗从南方4号医院出院后,显然恢复得很好,我开始在脑海里浏览《诊断与统计手册》上的人格障碍列表。他并不完全符合边缘型人格或自恋型人格,但人们可以为依赖型人格提出论点,这些人反复如此沉重和快速地跌倒,以至于当失败时他们会自杀。
我问他有什么自杀计划,他列出了七、八种可能的自杀方式。这样,我知道保罗有资格再住院一次,或者至少我不能让他出院。丽贝卡很早就告诉过我急诊室精神病学是一种不同于我们所接触的其他环境的动物。
丽贝卡说:“关键是,每一次接触最终都归结为你是让病人入院还是让他们出院。”“你不能在急诊室做治疗。你给的药不会有什么效果。你所能做的就是决定下一个治疗地点。”
“那么治疗方面的遭遇呢?”用心聆听吗?难道你就不能改变现状吗?”我问。
“哦,是的。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回答道,丝毫没有讽刺或讽刺的意味。
接下来,我见到了黛博拉,一位54岁的女性,因患双相情感障碍而入院14次。在南方4号医院急性躁狂发作后,她最后一次出院时,她看起来真的很好。
她的房间很暗,窗帘拉在玻璃前面。
“黛博拉?斯特恩博士。我可以进来吗?”
我听到一声闷声闷气的回答,便把头探了进去。她的脸埋在枕头里。我在床边坐下,等她开口,但她没有。
“黛博拉,我们能谈谈吗?”
她慢慢地转过脸来看着我。
“我不能这样生活。我在吃药,这只会让我一天比一天郁闷。为什么会这样?”
她向我寻求指导,但我只有同感。
“我很遗憾发生在你身上。这种疾病。”
“我该怎么办呢?”她绝望地问。
“我们会照顾你的。”我回答。
我看过的三个病人,每个病人都有成堆的文件,但我决心在回到掩体做笔记之前,先看看分配给我的四个病人中的最后一个。
第四名患者是中年金格。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被一面墙上的镜子惊呆了,陷入了精神错乱的思维过程,她似乎在我给她的一面小镜子里得到了安慰。
然而,当我走进房间时,我突然意识到,包括镜子在内的她所有的财产都被保安藏了起来。她踱来踱去,自言自语,我听不懂。我没法让她看我,甚至连打招呼都不行。
我走出房间,四处打听,直到我找到另一面小镜子。我把它拿在手里,这让金吉尔停止了踱步,头一次抬头看着我。她伸出手,轻轻地把镜子从我手里拿了过去。
她看着照片中的自己,我看到她的脸绷紧了,嘴唇向下卷着。她把它扔在瓷砖地板上,它就裂开了。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仍然带着愁容,又开始踱步。
“我很抱歉让你过得很艰难,”我一边说一边把破碎的镜子捡起来。
我走出病房,告诉值班护士我马上给她点抗精神病药。
当我回到地堡时,丽贝卡似乎比刚开始当班时更加疲惫。
“恐怕没人做得很好,”我以报告的口吻说。
“写好笔记,然后继续前进,”她回答。“已经有四家新的咨询公司来了。”
作者注:本书基于我在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培训期间的经历。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已经获得了许多当事人的许可,我还更改了他们的名字和身份特征,以保护他们的隐私。我还创建了合成角色。在这本书中,病人的描述和病人的遭遇被故意修改,使他们无法辨认。
版权©2021,作者:亚当·斯特恩,医学博士。经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许可转载。现在可从HMH Books &媒体。
文章旨在传播新闻信息,原文请查看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1/09/a-day-in-the-life-at-an-er-psych-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