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的流行对杜克大学的研究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乎所有基于实验室的研究都暂时停止了,除了与抗击COVID-19直接相关的研究。恢复正常需要很长时间,恢复的过程将是渐进的,并将得到认真执行。
为了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1939年在《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The有用性)的文章。弗莱克斯纳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创始所长。在那篇论文中,他对研究型大学所获得的大部分知识进行了沉思。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说,对这类知识的追求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从而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改变我们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改变我们以前放弃希望的东西。这样的知识有时非常有用,但却用在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
 格雷戈里·格雷,医学硕士
格雷戈里·格雷,医学硕士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5亿确诊病例和5000万人死亡。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想想我们对流行病的理解已经走了多远,这些知识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应对能力。医学教授、杜克全球健康研究所(DGHI)成员格雷格·格雷(Greg Gray)等人多年来一直在悄悄研究病毒,包括家养动物农场和食品市场的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许多人认为,COVID-19病毒是从蝙蝠身上传播到人类身上的。格雷博士一直是研究这种潜在病毒大流行机制的全球领导者,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亚洲进行的,这些经验使他处于独特的地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困境。
从卫生政策的角度来看,杜克大学马戈利斯卫生政策中心主任马克·麦克莱伦在了解病毒和应对流行病的最佳政策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作为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他有将政策付诸实施的经验,他的声音在华盛顿的大厅里有分量。马戈利斯中心利用杜克大学的全体教员及其广泛的应用政策研究能力,在指导政策制定者应对covid19方面一直走在前沿。
通过像博士这样的学术领袖积累的知识。格雷和麦克莱伦敬畏地注意到,当今世界对病毒威胁的反应与100年前相比有何不同。虽然在今天许多人的生活中有重大的动荡和重大的困难,但由COVID-19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相对于1918年已大大减少。
COVID-19的一个看似不寻常的方面是,被该病毒感染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症状。然而,那些无症状的人会传播病毒并感染他人。虽然大多数人没有或只有轻微的症状,但也有一些人对COVID-19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有些人会很快死去。
这种对COVID-19的异质反应是传染病医学教授Chris Woods研究的病毒的一个特征。伍兹博士和他在医学院和工程学院的同事们,早在当前的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重点是人类宿主对病毒的基因组反应。对病毒的了解使伍兹博士和他的同事在理解COVID-19和指导临床反应方面发出了领先的声音。
由人类疫苗研究所的病理学教授Greg Sempowski领导的一个小组正致力于从sars – cov -2感染者中分离出保护性抗体,看看它们是否可以作为药物来预防或治疗covid19。他们正在寻找能够中和或杀死病毒的抗体,这种抗体被称为中和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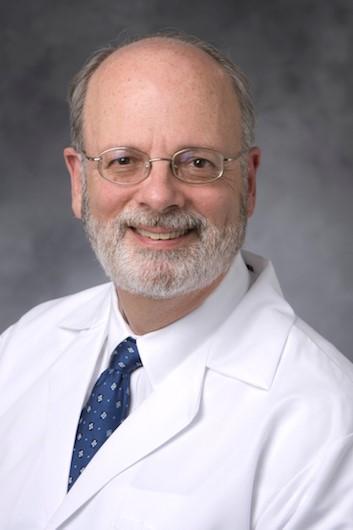 巴顿海恩斯,MD
巴顿海恩斯,MD许多人认为,只有针对COVID-19的疫苗才能真正让生命恢复正常。人类疫苗研究所所长Barton Haynes和他的同事在开发这种疫苗以提供人类对COVID-19的耐药性方面处于前沿。海恩斯博士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疫苗研究,现在这项工作处于对抗COVID-19的前沿。
自1918年以来,工程和材料科学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机械工程和材料科学教授肯·加尔(Ken Gall)带领杜克大学开发了3D打印的新应用,开发了创造性设计个人防护装备(PPE)的方法。这些个人防护装备正在杜克医院使用,并在全世界范围内用于保护卫生保健提供者对抗COVID-19。
上面讨论的许多工作,除了出于了解和适应病毒的愿望之外,都是从必须与病毒作斗争以延长人类寿命的角度出发的。
相比之下,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的学者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学者艾曼纽埃尔•查彭蒂尔(Emmanuelle Charpentier)分别提出了一个看似毫无用处的问题。他们想了解细菌是如何抵御病毒的。可能使这项工作看起来更无用的是,感染细菌的特定种类的病毒(称为噬菌体)不会引起人类疾病。没用的东西!这种工作只能在大学里进行。这项基础研究发现了一种有规律的、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这是一种针对病毒的细菌防御系统,可以作为操纵基因组序列的工具。出乎意料的是,CRISPR显示出了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编辑基因组的能力,有可能治愈以前无法治愈的遗传疾病。
生物医学工程教授查尔斯·格斯巴赫(Charles Gersbach)和他在杜克大学的同事们在基因和细胞治疗的CRISPR研究方面处于前沿。事实上,他正在与杜克大学外科教授和基因治疗专家Aravind Asokan合作,设计另一类病毒,将CRISPR传递到病变组织,这种病毒最近被FDA批准用于其他基因治疗。这种被改造过的病毒远非杀手,它对于让CRISPR进入正确的组织以一种以前被认为不可能的方式进行基因编辑至关重要。CRISPR技术有望治愈镰状细胞和其他遗传性血液疾病。它还被用于治疗癌症和肌肉萎缩症,以及其他许多疾病。在杜克大学,Gersbach博士也用它来治疗covid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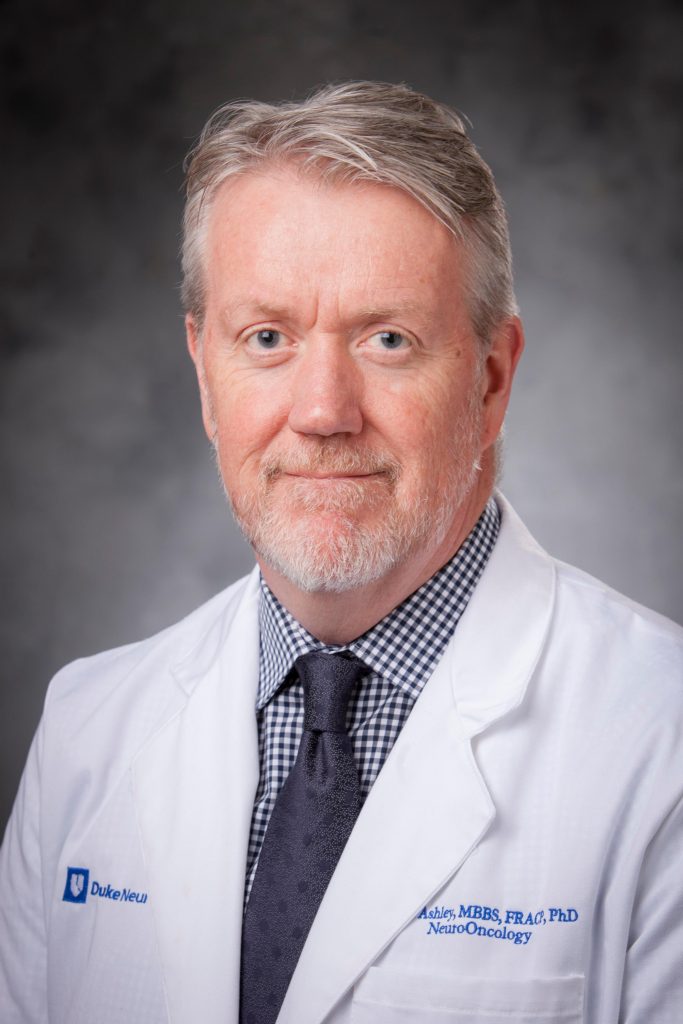 大卫·阿什利博士
大卫·阿什利博士在另一个看似奇怪的病毒使用中,杜克大学正在使用一种改良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来对抗一种脑瘤——胶质母细胞瘤。这项工作正在普雷斯顿·罗伯特·蒂施脑瘤中心进行,戴维·阿什利是该中心的主任。利用改良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刺激人类先天免疫系统对抗胶质母细胞瘤,并以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延长生命。但仍有许多基础科学问题需要克服。以脊髓灰质炎为基础的免疫治疗显著延长了只有20%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生命。为什么?回想一下上面讨论的伍兹博士的工作,以及我们自己对COVID-19的观察,并不是所有的人对病毒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这能解释免疫疗法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混合效果吗?目前还不清楚,不过阿什利博士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更好地了解宿主对病毒反应的多样性,并进一步改进免疫治疗,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COVID-19大流行是一项挑战,它正在扰乱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杜克大学正在进行的基础研究,我们对这种大流行的认识已显著提高,加快并提高了我们的应对能力。通过杜克大学的工程师和临床医生之间的创新合作,正在开发保护第一线医疗专业人员的新方法。此外,通过像CRISPR和免疫治疗
2这样的创新技术,
2病毒被用来拯救以前难以治愈的疾病的生命。
病毒可以是杀手,但它们也是科学上的奇迹。这是基础研究的前景;这就是杜克大学研究的影响。
“我们不会停止对
的探索,我们所有探索的终点将是我们开始
的地方,我们将第一次认识这个地方。
艾略特,四重奏

文章作者劳伦斯·卡琳,研究副总裁
新闻旨在传播有益信息,英文原版地址:https://researchblog.duke.edu/2020/04/14/dukes-fundamental-research-can-turn-viruses-into-mar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