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希拉·托比亚斯(Sheila Tobias)注意到数学领域的一些奇特现象。在她早期的一项研究中,这位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的毕业生,自称“学者活动家”,著有14本书,包括1978年的畅销书《克服数学焦虑》(Overcoming Math Anxiety),给小学生们一张纸,分成两半。一边,他们在做一道数学题;另一方面,他们写下问题给他们带来的感受。
“我完了,”一个人写道。“其他人都不是。我一定是错了。”
另一个人写道:“我还没说完。其他人都是。我一定是错了。”
许多人记得他们的父母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家没有人擅长数学。”其他人则回忆起站在黑板前,在同学的起哄和笑声中解不出一个方程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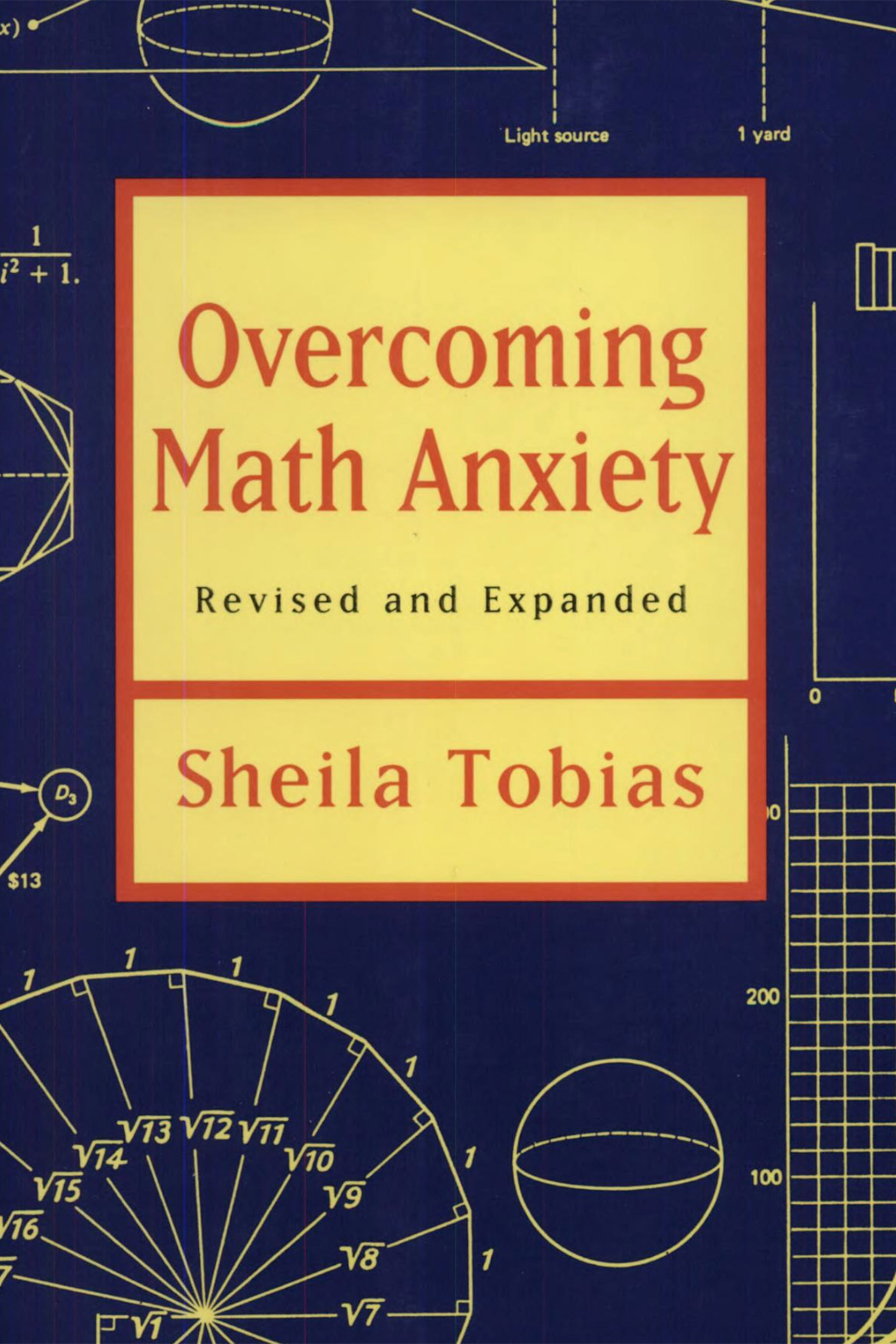
“数学焦虑症是一种严重的障碍,”托比亚斯在1976年《女士》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她的发现。它由母亲传给女儿,父亲也会带着逗乐的溺爱。(‘你妈妈从来不会结算支票簿,’他亲切地说。)”
时至今日,数学焦虑症仍然困扰着学生——尤其是那些属于该领域历史上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学生——这比平衡的支票簿更有利害关系。气候变化、流行病和不公正划分选区等威胁没有数学就无法解决。
“你无法开始理解这些问题,”托拜厄斯在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的一次演讲中说。就在一年前,她于2021年去世,享年86岁。(直到今年9月《纽约时报》刊登讣告,她的死讯才被广泛报道。)
自从托拜厄斯第一次描述数学焦虑对学生——尤其是年轻女孩和女性的影响以来,差不多50年过去了,他的论文被拉德克利夫学院施莱辛格图书馆收藏。然而,变化并不大。根据认知科学家Sian Beilock 2019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数学的恐惧》,近一半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表示,他们对数学“中度紧张”或“非常、非常紧张”,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报告称有中度或高度的数学焦虑。
“讨厌数学似乎能让人们走到一起,”哈佛数学系的导师雷希玛·梅农(Reshma Menon)说。“这不仅仅关乎我的学生。我会在杂货店和人见面,或者我会在优步上和司机聊天。当我告诉他们我教数学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天哪,我以前在学校很讨厌数学。’数学焦虑症在全世界都存在,而且非常非常真实。”
数学仇恨,或者被一些人称为“数学创伤”,就像普通的感冒:无处不在,难以追踪,难以治疗。
“数学领域有一个天才神话,”哈佛大学数学导论主任布伦丹·凯利(Brendan Kelly)说。“人们通常认为,成功需要一些天生的能力,一些不可教的品质,一些不可改变的特质。”
当学生们学习写故事或拉小提琴时,大多数人并不期望在第一次尝试时就能复制托尼·莫里森或Niccolò帕格尼尼。没有人会说:“我不擅长写作。”但在数学方面,同样是哈佛大学数学讲师的阿勒查·塞拉诺(Allechar Serrano López)说,“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决定了他们是适合数学还是不适合数学。”由于数学是进入几乎所有其他科学领域的大门,早期的印记可能会把学生挤出STEM的管道。
但天才神话并不是唯一的障碍。
根据上小学和中学的不同,上大学的学生有着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梅农指出,有些学校甚至不开设微积分课程。“在大流行期间,这些差异变得更大;现在的差距比以前明显得多。”
学校间的差异往往对低收入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梅农说:“这种差异导致学生自信心下降。“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有色人种和非二元性别学生感觉自己不适应这里。”
“数学领域有一个天才神话。人们通常认为,成功需要一些天生的能力,一些不可教的品质,一些不可改变的特质。——布伦丹·凯利,哈佛大学数学导论主任
数学家们可能会说,数学是一门精英教育,完全基于学生是否能解决问题。但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教育和机会的不平衡,还让教师们摆脱了困境。
梅农说:“我真的应该负责创造一个空间,让学生们觉得他们可以提问,分享他们的想法,慢慢变得更自信,克服他们的数学焦虑。”
这意味着缩小班级规模,开展团队合作,并对那些来自条件较差的学校或身份可能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的学生给予额外关注。
“我们的数学教育需要一种文化上的改变,”凯利说。“脆弱是一种挑战,对吧?在教室里举手说错是件很难的事。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可以感到困惑并分享这种困惑的空间。”
托比亚斯会同意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她就制定了《数学焦虑权利法案》(Math Anxiety Bill of Rights),其中包括:“我有权不理解”、“我有权不喜欢数学”、“我有权不把自我价值建立在我的数学技能上。”
今天的学生可能会补充说:“我有权被视为一个数学人。”
就连梅农也说,尽管她已经教了10年微积分,但她仍然在与冒名顶替综合症作斗争。Serrano López在她成为数学家和教员的道路上,考试和课程都失败了。乔治·普特南纯粹与应用数学教授、数学系主任迈克尔·霍普金斯承认,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
“大多数时候,我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他说。“我认为焦虑来自于当你处于无知状态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这是我非常重视的一种状态。”
霍普金斯和其他哈佛数学家认为,迫切需要进行文化转变,使数学教育更受欢迎、更具包容性。
“一切都岌岌可危,”Serrano López说。“我来自一个低收入家庭,我看到接受教育对社会流动性至关重要。”STEM职业不仅薪水更高;它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核战争和全球性疾病等生存威胁方面至关重要。
“如果这个星球要生存下去,”托拜厄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
“这根本不是他们的错,对吧?”梅农说。“正是我们建立这个体系的方式,让他们觉得自己完全不受欢迎。如果我们因为这种分歧而失去这么多有才华和聪明的人,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文章旨在传播新闻信息,原文请查看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2/11/the-myth-of-the-math-p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