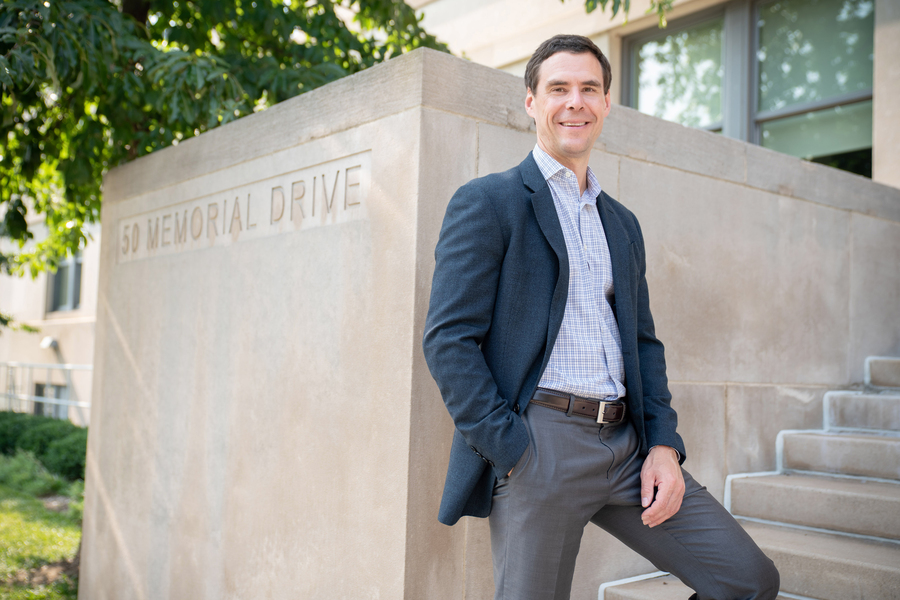
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土地,但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与1940年左右出生的人相比,今天在劳动力中工作的人比他们的父母赚得更多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该国某些地区的经济流动性比其他地区大得多。即使其他条件相同,种族和族裔群体之间的流动性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Nathaniel Hendren教授博士’12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作为一名今年夏天刚刚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亨德伦与人合著了一系列已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具有重要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当今美国的机会条件。
例如,1940年出生的人中有92%的收入高于父母,但1984年出生的人中只有50%的人这样做,中产阶级经历了最大的变化。研究表明,这只是由于GDP增长率的变化,更多的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方式,限制了中产阶级的收益。
人们居住的地方也会影响他们的前景。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长大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最低五分之一的儿童达到顶层五分之一的可能性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最低五分之一儿童的可能性的三倍。所有这些都与种族和民族相互作用;即使考虑到父母的收入水平,黑人男孩成年后的收入也会低于99%的美国人口普查区的白人男孩。
“这引发了很多问题,关于历史[问题和]政策做了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导致今天的低收入流动性,”亨德伦说。“这是一个受我们制度和政策影响的景观。
在我们的地方。亨德伦的研究表明,社区层面对经济成果的影响,与儿童在特定地方生活的年数相对应。
“我们是我们长大的社区的加权平均值,”亨德伦说。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政策旨在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机会。在他的研究的另一个领域,亨德伦开发了用于比较项目有用性的新工具,同时担任政策影响(Policy Impacts)的创始人和联合主任,这是一个支持循证决策的无党派团体。
“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的50年里,提供最大回报的政策是那些对孩子,特别是低收入儿童进行直接投资的政策,”亨德伦说。“这不一定是给父母的现金转移或可能溢出的事情。这是对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健康的投资,对这些孩子的直接投资。
前往比赛
亨德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队伍代表了理智的回归,因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不过,他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开始对该领域产生兴趣,在那里他主修数学和经济学。
“我一直喜欢你可以正式地用数学描述社会互动或人类行为,数学的精确性约束了你所拥有的理论和你可以做出的陈述,”亨德伦说。
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课程后,亨德伦与Daron Acemoglu和Amy Finkelstein合作,担任他的主要顾问,撰写了一篇关于保险市场研究的论文。
“我来到这里,再也没有回头。我发现我喜欢做研究,那时它已经进入了比赛,“亨德伦说。
从那以后,亨德伦一直在以赛车的速度进行显着的研究。作为2012年新晋的研究所博士,亨德伦加入了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并很快开始关注机会和社会流动性问题。他与包括Raj Chetty,Lawrence Katz和Emmanuel Saez在内的一系列合著者合作,在主要期刊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
亨德伦还与芬克尔斯坦合著了一些关于健康保险计划影响的论文,他有时会研究市场失灵问题。但他的大部分工作都直接集中在社会流动性上,包括旨在测试个人政策理念的研究。
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Chetty,Hendren和Katz研究了“转向机会”计划,该计划为贫困家庭提供代金券,以帮助在低贫困社区提供住房,并发现参与该计划的家庭中的孩子最终实现了31%的收入增长成年。
在即将发表在《 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相关论文中,Chetty,Hendren,Katz,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Christopher Palmer和其他合著者在西雅图地区进行了住房券计划的实验。通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导航员”,提供房地产经纪人和财务顾问的一些服务,参与者对代金券的使用从15%增加到53%。
“当你为人们提供这些导航器时,我们发现效果非常大,”亨德伦指出。“对于如此大的生活变化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低接触的干预。
亨德伦指出,这种结果“排除了这个关于[住房]隔离如何由隔离者的偏好驱动的故事。我认为这是由机构强加给他们的限制以及人们[改变]游戏规则所驱动的。他补充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很多人希望生活在促进孩子向上流动的社区,并愿意为此做出权衡。
衡量有效的方法
亨德伦指出,从历史上看,住宅隔离已经根植于美国生活中的汹涌潮流中;即使在20世纪中叶所谓的大迁徙期间,数百万黑人家庭离开了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南部,他们到达北方城市也导致了从城市到郊区的广泛“白人逃亡”。像“走向机遇”这样的个别项目可以奏效,但在创建鼓励社会流动性的可持续多元化社区方面存在巨大的障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创造了向上流动高的地方,但它们是带有障碍的飞地,阻止[许多]人进入这些地方,”亨德伦说。
然而,鉴于政府已经制定了广泛的措施,旨在鼓励教育、经济发展、公共卫生、更清洁的环境以及许多其他可能影响社会结果的事情,亨德伦近年来一直在努力重新定义这些计划的底线衡量标准。
“我们正试图为政策的作用创建连贯一致的衡量标准,”亨德伦说。从教育到环境再到公共卫生等主题的研究使用不同的指标来评估政策,但亨德伦和经济学家本·斯普伦-凯瑟(Ben Sprung-Keyser)努力将它们统一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中,开发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公共资金的边际价值”的指标,并将其应用于133种不同类型的政府政策。
“这真的是一个简单的指标,”亨德伦说。“政府在净额保单上花费的每一美元,以美元计算,该政策为其受益人提供了多少好处?”
这项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儿童身上的支出每花费一美元就能提供最大的额外回报。这并不是说其他程序不值得。但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这种分析来分配预算。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明显有效的政策理念也很难通过任何特定的立法院。尽管如此,亨德伦指出,手头有坚实、确凿的事实和机会、流动性和政策供每个人使用是有价值的。
“政治是粘稠和混乱的,”亨德伦说。“我对社会变革和政治的看法可能有点乐观和乐观,但如果我没有这种观点,我就不会保持动力。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我们的最佳估计来衡量我们认为正确的权衡,并揭示政治家必须支持一项政策而不是另一项政策的隐性偏好,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取得一点进展。
新闻旨在传播有益信息,英文版原文来自https://news.mit.edu/2023/nathaniel-hendren-social-mobility-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