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微生物学家Cameron Myhrvold刚刚完成加入普林斯顿大学教职的第二次面试,他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介绍了革命性的CARMEN系统,该系统同时测试170种最常见的人类感染病毒,包括当时的新型冠状病毒。当时,只有39种病毒得到了fda批准的诊断检测。
梅尔沃德是2011年毕业的,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在这场大流行让他的工作具有全球意义之前,他在那里深入研究冠状病毒已有多年。
他说,他对病毒的兴趣很早就开始了。他的父亲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1983年的博士,他告诉过他关于埃博拉的事情。他说:“我真的对病毒很感兴趣——它们是如何让我们生病的,但它们是如此简单,只有这么少的基因。”“我一直对技术很感兴趣,所以我认为我所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会有技术成分。”
2021年1月,梅尔沃德加入了分子生物学系,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最新的COVID-19专家之一,也是越来越多跨越基础研究和突破性技术发展边界的研究人员中的一员。

Myhrvold使用CRISPR-Cas13来检测和切割RNA (DNA的鲜为人知的单螺旋表亲)。
“Cameron使用基因组编辑技术来了解、监测、诊断和摧毁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病原体,”Squibb分子生物学教授兼系主任Bonnie Bassler说。“他惊人的新技术使他和他的合作者能够解决当前生物医学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重要问题。”
他的武器库中的一个关键武器是CRISPR-Cas13。如果这听起来很耳熟,那可能是因为在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被CRISPR-Cas9的科学家们获得了,CRISPR-Cas9是一种允许精确切割DNA的基因编辑工具。但对于Myhrvold用来检测和切割RNA (DNA的不太为人所知的单螺旋表亲)的工具CRISPR-Cas13,人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Myhrvold和该领域的其他人已经确定了四种基于Cas13的技术,它们的工作方式略有不同。一个就像手术刀一样,小心翼翼地剪断单个RNA链,就像Cas9切割DNA一样。另一种变体用其他蛋白质标记RNA链,包括一种可以跟踪RNA的荧光蛋白。第三种方法是使用一种名为ADAR的蛋白质一次编辑RNA中的一个“字母”——这是一项非常令人兴奋的生物医学进展,因为许多疾病都是由遗传密码中一个“拼写错误”的字母引起的。
第四种变体更像忍者之星而不是剪刀;它有一个“超速”模式,可以摧毁所有附近的有害RNA链。Myhrvold说:“我经常用碎纸机来比喻,因为你把你想要销毁的特定东西输入进去,然后嘣的一声,它们就被粉碎了。”
一些简单的生物体,包括许多病毒,用RNA编码它们的蓝图。这意味着Myhrvold的碎纸Cas13应用程序可能成为一种抗病毒治疗疾病,包括艾滋病毒、普通感冒、流感和COVID-19。
“基于cas13的抗病毒药物还需要很多年,但这绝对是我们感到兴奋的领域,”Myhrvold说。“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方法,因为只要我们能将其输送到你身体正确的部位,从而有效,我们最终可以治疗感染你身体这个部位的任何病毒。也许下一次爆发是流感,就像1918年那样,又或者是埃博拉或者其他完全不同的疾病。我们希望有多种多样的工具供我们使用。”
利用RNA的多样性
多功能性的秘密在于RNA本身。与保持恒定大小和形状的DNA不同,RNA以不同的长度和形状出现,在构建和维持人体的各种系统中扮演多种角色。
DNA是一种双螺旋链,它保存着你身体和大脑每一个微小部分的蓝图,多年来一直吸引着遗传学家。但是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将他们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单链RNA上。如果DNA是你身体的蓝图,那么蛋白质就是承包商、砖瓦工和水管工,将蓝图赋予生命。几十年来,RNA一直被视为一个简单的翻译器,以蛋白质可以阅读的形式传递DNA指令。现在,科学家们正在发现RNA可以完成的许多其他工作,包括做一些蛋白质的工作。
“如果你看看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有所有这些伟大的工具来研究DNA,这些工具真的是革命性的,包括Cas9。我希望看到我们说,‘让我们再做一次,但是在RNA水平上,’”梅尔沃德说。“然后也许在几十年后,我们将讨论对蛋白质进行这样的研究。”
这种技术目前还不存在于蛋白质领域,但梅尔沃德暗示,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他的职业生涯的特点是拒绝被技术的局限所阻碍;他拥有7项专利,还有3项正在申请中。
梅尔沃德的实验室已经有人从事技术开发工作,他正在寻找具有广泛专业知识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来构建这个平台。
“我们在普林斯顿做的很多最好的科学研究都是跨学科的,”他说。“当我在这里学习时,我是综合科学课程的一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工作方式。我喜欢这些跨学科的合作项目。”
除了在分子生物系的主要工作,Myhrvold还隶属于化学和生物工程系以及化学系。他说,在他建立实验室的过程中,他正在寻找来自这些部门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还有定量和计算生物学,Lewis-Sigler综合基因组学研究所,甚至物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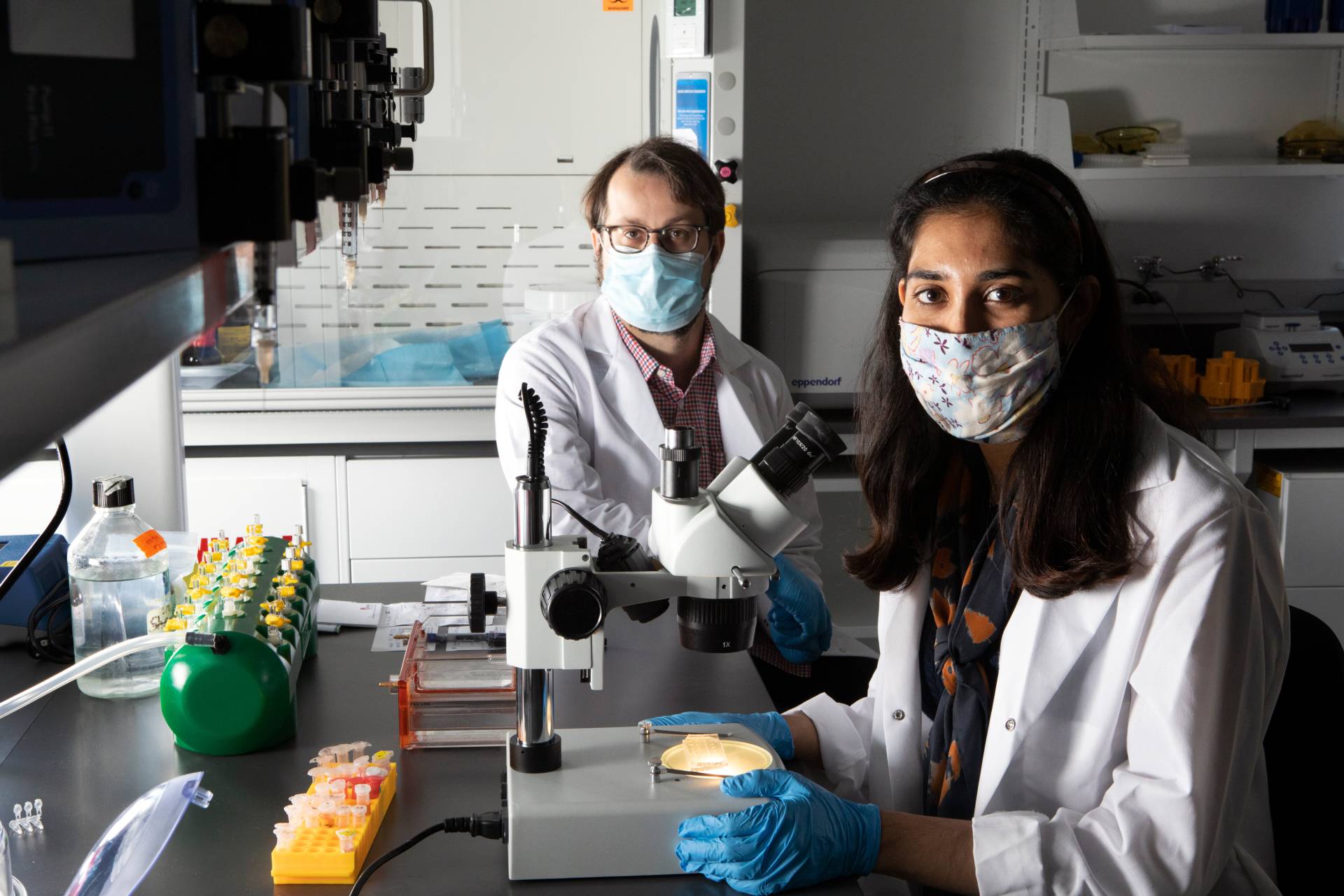
“卡梅伦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梅尔沃德实验室的研究生施鲁提·夏尔马(右)说。“你真的会觉得有人在那里支持你,帮助你成功。”
梅尔沃德称自己“非常兴奋”能够与之前的导师以及部门内外的新教员开展合作。他开始与另外两个分子生物学教授的合作——Zemer Gitai,埃德温·格兰特康克林生物学教授伊丽莎白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达蒙b·菲佛生命科学教授,他是在与几个潜在的研究伙伴从部门和项目在大学。他与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院长、Stephen C. Macaleer ’63工程与应用科学教授Antoine Kahn共同指导研究生Shruti Sharma。
“卡梅伦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的指导让你有信心取得成功,”夏尔马说。“我很欣赏卡梅隆在生物科学之外还精通自然科学。因此,他的项目涉及面很广,从理解新科学到设计服务于更大目标的技术。我正在寻找它。我在想,‘我学过物理,我想把我的知识应用到更人道主义的事情上。’”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梅尔沃德专注于分子生物学,并完成了定量和计算生物学证书,随后赢得了房利美和约翰·赫兹基金会(Fannie and John Hertz Foundation)提供的25万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奖学金,供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之后,他在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做博士后工作,领导他的是普林斯顿大学1978届校友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之后他回到普林斯顿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
“这是一条相当长的轨迹”
“我们系的一名本科生现在成了我的同事,这让我非常自豪,也有点伤感,”系主任、梅尔沃德的前高级论文导师巴斯勒说。“我们的其他教员都不是本科生。这与他在我实验室学习吸液管时的轨迹相当吻合。”
她回忆说,当梅尔沃德和她一起写大三和大四论文时,“他总是极具创业精神和创造力。”现在,十年过去了,他的投资组合是技术发展和基础科学的非常有趣的结合。”
在很多方面,梅尔沃德的研究之旅都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说明纯粹的、由好奇心驱动的科学是如何演变成具有非常具体的生物医学应用的东西的。“我认为这将永远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说。“我喜欢在这里研究这么多不同的基础科学问题,与这么多了不起的人合作,我也将继续这项病毒威胁的工作,及其具体的应用,因为RNA病毒对人类健康是如此的威胁。”
他说,即使过了18个月,他仍然因为疫情而失眠。“在很多国家,疫苗几乎是不存在的,我担心在未来几个月里,这将反过来影响我们。很多美国人的行为就好像COVID已经过去了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这种心态让它东山再起。我担心的不仅仅是Delta或Lambda变体,我担心的是希腊字母表的其余部分。我想我们要用完希腊字母了。然后呢?这将是一场军备竞赛,希望世界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迅速生产和分发足够的疫苗,这将是没问题的,但我担心。”
在组建团队继续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梅尔沃德致力于让学生们始终站在实验室研究的前沿。“显然我有一点偏见,但我爱这里的本科生,”梅尔沃德说。“我在读本科时就喜欢做研究,对我来说,让本科生成为实验室的成员是很重要的。第一年有点棘手,尤其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物流,但已经很有趣了。”
2022届的克里斯托弗·关(Christopher Guan)是第一个加入梅尔沃德实验室的本科生。
关天朗说:“我最初联系卡梅伦是因为我发现他的研究非常有趣和独特。”“在处理新设计时,他给了我难以置信的创作自由,他总是会选择指导我的思维,而不是规定一个正确的方法。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总是在他的实验室里学习。”
“我给了克里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项目,”梅尔沃德说。“我当时想,‘如果失败了,也不是世界末日,但如果成功了,我真的很高兴看到它的未来。’”
梅尔沃德在普林斯顿的人脉涉及多个方面。他的父母是在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的——他的父亲攻读应用数学,而他的母亲攻读浪漫语言和文学——在大学本科时,他的双胞胎兄弟康纳(Conor)和他一起在2011届入学。
“能回来真是太好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