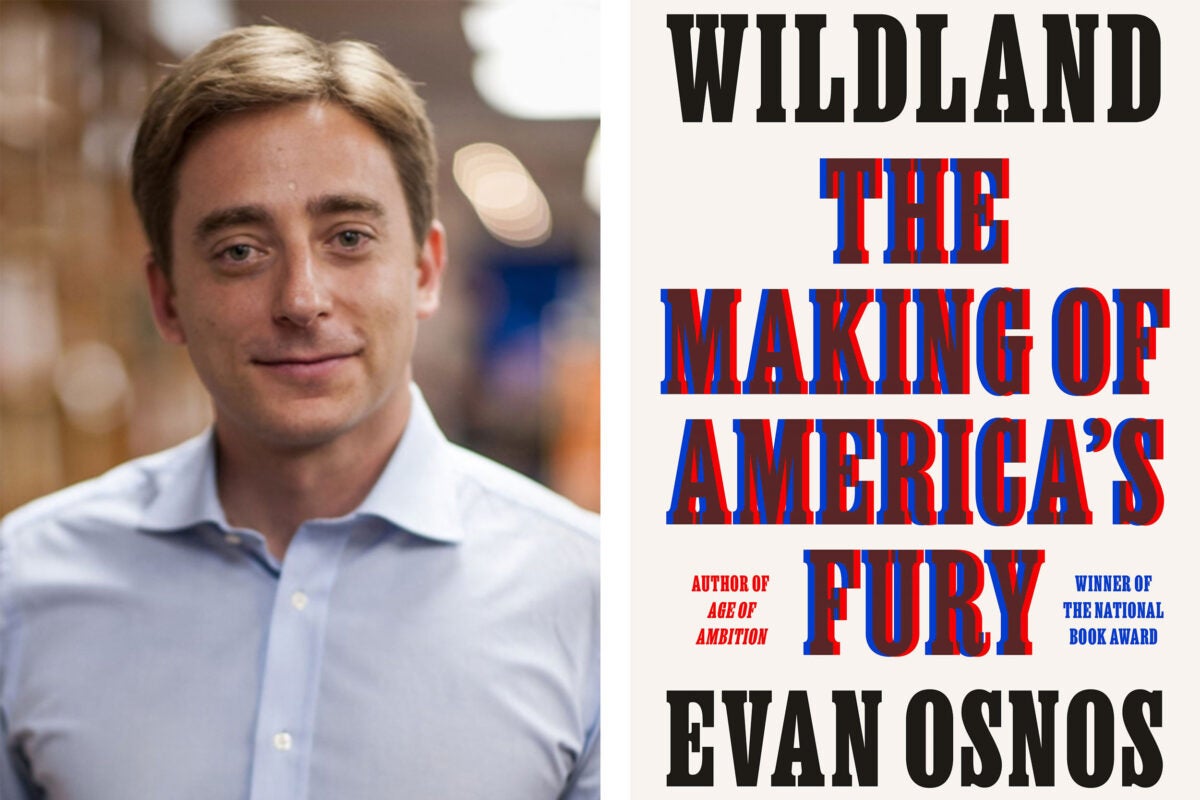摘自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 98年的《荒野:美国愤怒的形成》(Wildl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Fury),他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特约撰稿人,由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
在旧金山以北三小时车程的一个山坡上,一位牧场主涉水穿过一片金色草沙沙作响的草地。他的名字叫格伦·基尔(Glenn Kile),他住在美国西部一片受到大自然眷顾的狭长地带,当地人称之为巴洛凯(Ba-lo Kai),意思是“翠绿的山谷”。但在这一天,地形无情。温度是103华氏度,连续几天都在三位数。加州历史上最热的夏天都是在过去20年里到来的,青翠的山谷里的田野里散发出一股枯干的气味和稻草的噼啪声。
在离家一百英尺的地方,牧场主看到他脚下灰黑色的土地上有个小洞,便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地下黄蜂巢的口。他举起一把铁锤,把一根生锈的铁桩敲进洞里封住。但是金属之间的碰撞发出了火花,火花击中了田地,田地开始燃烧起来。
在半个小时内,大火蔓延至20英亩(约1.6公顷)的范围,蔓延至地平线上干涸的森林和散落的房屋,消防员称之为“荒野”——一个近乎完美的火种领域,与其说是一个地方,不如说是一种状况。牧场主的火花点燃了加州历史上最大的荒野大火,这个记录很快就被打破,然后又被打破。他们将其命名为“门多西诺复合火灾”,这场大火持续了一个月——由风和火焰组成的喷射引擎,吞噬了两倍于纽约市的面积,这是全球变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这场大火最终被扑灭时,加利福尼亚州裁定基尔对这场灾难不负责任。他点燃了火花,但灾难的根源更深。这场大火是几十年来各方力量聚集的高潮。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中国革命家毛泽东的一本书中关于政治的一句老话。毛写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对美国知之甚少,但他知道政治的残酷真相。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的那些年里,我生活在华盛顿,经常会想到那种即将被烧毁的景象。有时这感觉像是隐喻,有时又像是事实。但最终我把它理解为另一种东西——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寓言,当这片土地和人民似乎反映了另一方的愤怒。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发生一年多后,我离开了美国。这个国家正准备在伊拉克开战,我在巴格达、开罗和中东其他地方报道。几年后,我在北京定居下来,在那里我遇到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萨拉贝斯·伯曼(Sarabeth Berman),她曾作为一名年轻的戏剧和舞蹈制作人出国。我们结婚了,最终准备回家。萨拉贝斯说,如果我们在国外呆得太久,我们就会发现很难回去了。
2013年,我们计划搬到华盛顿。回家总会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20世纪40年代,在报道了欧洲的战争之后,作家约翰·冈瑟回到了美国。他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内部》中写道,有时他觉得自己是“来自火星的人”。在冈瑟的例子中,他家的一些特征让他感到不安;他写道,南方的种族隔离“比我在欧洲犹太人区,甚至是华沙看到的都要严重”。但其他的遭遇让他兴奋不已。在他的全国旅行中,他开始问人们,“你最相信什么?”他被告知:工作、孩子、托马斯·杰斐逊、上帝、黄金法则、勾股定理、高关税、低关税、更好的农产品价格、幸福、良好的道路,还有圣诞老人。但用他的话说,最常见的回应是,“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那就是人民。”
2013年7月7日,萨拉贝斯和我降落在杜勒斯国际机场。在护照检查处,我拿起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欢迎来到美国”。它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出版,封面照片是华盛顿纪念碑和盛开的樱桃树。宣传册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很高兴你决定来美国旅游、学习、工作或停留。”
我开始记录我离开的这些年里发生的变化,包括一些微小的细节。经过服装制造商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的橱窗,我注意到这家公司正在销售翻领上预先别有国旗别针的西装。一位公司发言人告诉我,这是为了给美国制造的西装做广告。该公司在2007年采取了这一做法,当时共和党人抨击时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没有佩戴国旗胸针。
其他变化感觉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难把握它们的完整维度。2013年,美国在移民和多样性的漫长演变中跨过了一个门槛:非白人新生儿的数量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超过了白人新生儿的数量。最初,这一差距几乎察觉不到,在那一年出生的380多万婴儿中,不到1000人。但它开始增长。作为一名难民的儿子,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里程碑,是复兴的标志,但我可以看到,许多其他美国人不这样认为。
在一些变化中,我最惊讶的是人们对它们的完全适应。一天早上,我在等美国铁路公司(Amtrak)的火车时,车站登机区的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公共服务通告。画外音解释说,如果有人开始向我们开火,我们应该“逃跑”或“找掩护”。屏幕上,一个满头白发、身穿蓝色西装的演员蜷缩在一根柱子后面。它说,作为最后的手段,采取行动:“大喊,并寻找周围的物体,包括你的物品,投掷和使用作为临时武器。”
平均每九周就发生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几乎是十年前的三倍。仅仅六个月前,康涅狄格州纽敦市一名20岁的男子在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杀害了20名儿童和6名教师,这是最令人揪心的事件。但在美国政治中,这一事件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政客们表达了“想法和祈祷”,但国会试图通过新的枪支管制措施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我环顾等候区时,人们都在专注于其他事情。我觉得自己像甘瑟的火星人。
这个国家对2001年9月11日的创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当基地组织(Al Qaeda)摧毁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双塔时,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写道:“从曼哈顿下城我的窗户,我看到了21世纪的开始。”12年后,这一事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象征力量。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美国人遭到极右翼恐怖分子袭击的次数是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的两倍多,但当研究人员在2016年要求人们估计美国穆斯林的比例时,美国人平均估计为六分之一。真正的数字是100分之一。
我开始注意到恐惧已经深入我们的政治生活。出国之前,我住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克拉克斯堡,那是阿巴拉契亚的一个小城市,我在当地的报纸《指数电报》工作。9月11日之后的第二天,编辑们发表了一篇谦逊的声明,承诺致力于一个美国人告诉自己的故事:“政府的反应绝不是一个小镇的日报能提出的,”他们写道,但有一件事必须清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以其多样性、思想交流和容忍不同意见的意愿而自豪”;这些攻击必须“强化我们的理想,而不是粉碎它们”。那个月,在西维吉尼亚州普林斯顿市,有人亵渎了一座清真寺——破坏者画了一幅私刑的图画,还画了一个“贾马尔”的名字——邻居们聚集起来为这座清真寺辩护,而当地人的反应成为了他们的骄傲。
但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西弗吉尼亚州有五分之一的民众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2001年之后有所减少的仇恨犯罪又在攀升。2013年,有人再次破坏了这座清真寺,但当时当地人的反应比较平静。教堂谴责了这起袭击事件,但警长表示,这起事件不符合仇恨犯罪的门槛。在西弗吉尼亚州生活了几代的穆斯林描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四年后,在西弗吉尼亚州国会大厦举行的一场共和党集会上,有人悬挂了一幅正在燃烧的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海报,以及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Ilhan Omar)的照片。奥马尔是国会首批穆斯林女性议员之一。配文写道:“我就是你忘记的证据。”)
美国生活中的这些裂痕是更大裂痕的一部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收入中值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但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27个州由于缺乏资金来修补坑洞,他们不得不将一些铺就的道路改为土路。与此同时,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杰夫·贝佐斯这三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美国后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贝佐斯每小时的收入为149353美元,比普通美国工人三年的收入还要高。
当科学家报告预期寿命下降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西弗吉尼亚州麦克道尔县的男性预期寿命已降至64岁,与伊拉克的水平相当。在邻近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男性预期寿命要长18年。之间的深渊美国生活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消失的共同点可能不再携带美国机构的重量,一个前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警告当他告诉一个朋友,“我们可能有民主,或者我们可能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我们不能两者兼得。”
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它正在失去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设想共同利益的能力,一种相信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所说的“命运的单一外衣”的能力。他写道:“任何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事,都会间接影响所有人。”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谴责“恐惧本身”的诱惑80年后,美国人并没有否认他们的恐惧;他们宣布并付诸行动。犯罪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然而,在过去20年里,获得携带隐蔽枪支许可的美国人数量增加了近两倍,达到1300万人,是美国警察人数的12倍多。在奥巴马为他的言论道歉很久之后,这些话不再被视为一种侮辱。枪支展出售的T恤上写着“骄傲、痛苦、执着”的标语。
当我2003年移居国外时,CNN和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在黄金时段收视率相当,是竞争对手。11年后,福克斯与竞争对手分道扬镳;它每晚的收视率是现在的三倍,它还帮助催生了新的政治词汇,尤其是关于移民、安全、种族和联邦政府的角色。
10月1日,在我回到美国工作的第一天,政府在17年里第一次关闭。严格地说,它的关闭是因为国会的共和党成员试图废除奥巴马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福利,但关闭的真正目的是诋毁总统的标志性立法,团结信徒,并为即将到来的竞选筹集资金。这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上的反抗行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当时,种族隔离主义的民主党人拒绝接受联邦法院和国会的裁决。
16天后,共和党人让步了,政府重新开放。政府关闭给美国纳税人造成了大约2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笔钱足够让一个漫游者往返火星8次。即使在国会复会后,它仍然几乎完全瘫痪,因为华盛顿的许多当选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管理政府的工作本质上是与自由相冲突的。一开始人们对低税收和有限政府的信念,在利润和政治机会的压力下,变得更加坚定,从根本上蔑视联邦权力。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表示,评判立法者的标准不应该是“我们制定了多少新法律”,而应该是“我们废除了多少法律”。
在我看来,政府停摆标志着美国政治正逐渐浮出水面。一天天地过去,华盛顿与它所代表的国家的共同点越来越少。国会议员中有82%是男性,83%是白人,50%是百万富翁。而这个国家却不是这样。当我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旅行时,人们本能地认为政客的言论是自私的或腐败的。1964年,7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普遍信任政府;到2014年,这一数字大幅下降至18%。美国的政治形势已经为一场野火做好了准备。有人要来点火花了。
从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宣布竞选总统的那一刻起,他就是美国痛苦的一个症状,就像它的任何原因一样。他通过将政治尽可能地国有化,将最具爆炸性的问题转化为事关生死存亡的摊牌,从而将相距遥远的支持者团结起来,赢得了胜利。尽管他们为他对政治规范和政治文化的蔑视感到高兴,但更多的美国人对他感到震惊;他们为一个似乎已经脱离了某些最深刻的承诺、正在偏离历史判断的国家感到悲伤。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在2020年点燃,当时冠状病毒大流行产生了不同种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一名警察在膝盖下杀害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发了对美国权力配置的全面对抗。到了年底,政治屈从于暴力,美国人开始质疑,他们是否对民主机制失去了太多的集体信心,以至于可能永远无法恢复。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段时间里,美国遭受了两起对自身意识的袭击: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以及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失去了对共同利益的愿景,失去了将联盟视为大于各部分之和的能力。内战结束一个半世纪后,美国再次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美国神话的失败在华盛顿变得格外生动。但更深层次的起源和影响远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首都的事件只是偶尔闯入,就像火焰舔舐地平线。
版权所有©2021,作者Evan Osnos。保留所有权利。
文章旨在传播新闻信息,原文请查看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1/10/when-americans-lost-their-vision-for-the-common-good/